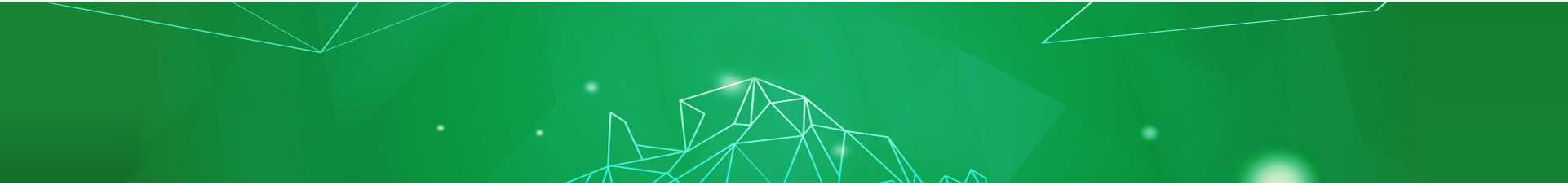

在追逐“贵族生活”的消费时代,人们很容易片面地把“贵族”物化为豪宅、豪车、小三和其他可供炫耀的奢侈品,甚至是为所欲为的特权。其实,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贵族还是传统中国的乡绅,关于他们的第一个关键词,无疑是“责任”。
顺德,曾经是中国乡绅体系发育最完善的区域。从顺德的故纸堆中,我们轻易就能发现历代顺德乡绅们的耀眼的人性光辉:他们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以顺德公益、地方公益、宗族公益为第一要务,克己、奉公,推动顺德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繁荣。
稳定柱石
顺德乡绅,是保持地方稳定的柱石。
作为顺德名门望族的代表,大良龙家乡绅辈出:26岁就高中进士的龙元僖,在历任京官和地方官后,四十余岁即“官加二品,赏戴花翎”,相当于今天的资深部级官员,他颇能代表能量极大的乡绅,在地方稳定层面为顺德奉献责任。
龙多以“士绅”的身份出现在顺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舞台上,他在大约44岁左右(1853年)的时候回到广东,此时,太平天国已经攻克南京,晚清风雨飘摇、时局晦涩。同年,以陈吉为首的顺德三合会(源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称为“洪门”,今天已经是华人世界首屈一指的黑社会组织)已经攻陷了包括大良的顺德大部,杀死多名顺德地方官员和清廷驻顺德军官,当时顺德一把手马映阶躲避在绅士家后被陈吉绑架。陈吉以保护乡闾的口号攻陷大良后,居民、商店、当铺遭到焚毁和洗劫,并开列单据向居民勒索,维持顺德经济活动的流通资金几乎完全被榨干。
龙元僖对此非常震怒,责令广东官兵迅速收复大良。1854年,陈吉将大良所有的粮仓劫掠一空。痛定思痛,龙元僖决心抛开无能的正规部队,建立地方武装以拱卫地方。龙被中央批准设立顺德团练局,并捐出龙氏大量家产作为首倡,在顺德“筑台募勇,购船置械,肃清余匪”,并使顺德地方政府恢复正常运转。顺德团练后来还在中山、番禺等地设立分局,给整个广东的三合会和流窜在南海的大小海盗以致命打击,使当时的大良,成为广东军事重镇。
龙利用北京和广州的官场人脉,先后六次请求广东省政府减免顺德农民税收,使顺德经济得到了休息生养的机会,在中山县与顺德县的土地所有权纠纷上为顺德谋利,客观上为顺德后来成为“岭南丝都”、“广东银行”奠定了基础。但在“农民起义”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陈吉被视为农民起义的英雄。虽然是清朝同治中兴中的杰出官员,也是顺德有名“士绅”的龙元僖,却被历史定格在陈吉的对立面,今天顺德人评价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有益顺德民生,是一个功罪互见的人物”。历史反覆无常,令人唏嘘不已。
制约政府
龙元僖级别的乡绅,实属凤毛麟角。在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上,承担大部分责任的仍然名不见经传的“小乡绅”。通常情况下,顺德乡绅在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领域,对几年一任的“流官”和政府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因为历史上“八百里路不为官”,再加上官员几年一任,官员对地方没有认同感,也缺乏责任感,所以官员们本能地想在地方上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顺德地处南国,方言驳杂难懂,“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而且很少本地人会讲普通话,那些走马上任的地方官员,难免有耳如聋、有目如盲。希望这些与群众基本沟通都比较困难的最高行政长官能主持公道,的确非常困难;而且,当时的顺德政府非常精简,大约只有9名吃皇粮的公务员,这还因为顺德人口众多,一个普通县的官员编制大约只有5名。要让这9名官员能管理百万左右的人口,而不依赖乡绅和家族长老的民间威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明朝嘉靖年间的知县胡崇德,志载“娴于言辞,上官以为能,然贪鄙暴酷、淫刑盗贪,笞死良民以千计”,在他手下当差的衙役,也搜刮百姓成为富翁,后来顺德乡绅向御史联名反映情况,胡因此丢官。胡崇德只是顺德一个暴虐的最高行政长官。清朝康熙年间,顺德知县刘鹏“耽酒任性,糊涂公事”,加上不了解顺德方言,在他手下服役的公差,就私造刑具,设立“吹箫引凤、金鸡独立、美人照镜、斑鸠点水”等酷刑,打了原告打被告,受苦百姓叫苦连天,不得不向公差贿赂银钱,钱少的甚至“献妻跪女,以求脱纲”。在他手下当差的衙役,个个身家巨万。勒流贡生伍谦吉就绘图上访,“督抚发指震怒,捕而按治之”,刘鹏因此被削官为民,“家业倾尽,其子流落广州”。
衙役欺凌百姓,历史上各地均极常见。由于过去的衙役不是公务员,属于服劳役的苦工一类(过去的百姓除了交税,还要服役),素质参差不齐;并且顺德方言在初来顺德的人耳中晦涩难懂,顺德人多数也听不懂县令的方言,狡猾的衙役就以“土音代传为名”,愚弄知县和百姓,屡屡颠倒黑白,让打官司的百姓有苦说不出。后来顺德乡绅联名制订警告“初任官员为政注意事项”,并在县衙前刻牌铭记,让初到顺德的官员有所提防。
过去的地方官员执掌民政诉讼裁判大权而缺乏制约力量,极易让地方百姓受到伤害。当遇到这种情况,乡绅们就为了群众利益向上级官员弹劾知县,迫使几年一任的官员们不敢胡作非为。
热心公益
当然,过去的顺德乡绅发挥的作用,不仅仅在危急关头扮演“解民倒悬”的侠义角色。他们的更重要的作用,广泛地发挥在教育、教化、交通、治安、慈善等公共事业领域。
历史上的顺德,书院、学社众多,但除了凤山书院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之外(由教谕主管,相当于今天主抓宣传和教育的常委、副区长),其它的鼓楼金锋书院、大洲钟山书院、鸡洲西园书舍、陈村西淋书院、乐从葛堡书院、马齐敦和书院、桂山书院和其它社学均由乡绅联合当地宗族长老(顺德俗称太公)创办。至于以开蒙化愚的为主的私塾,则属于宗族内部事务。乡绅除了在创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外,还必须到各大小书院充当义务教师,定期或不过期为儒生们讲学,大部分都向书院捐献学田(学田租赁收入供书院延请讲师、周济贫困学生),在乡绅的带动下,商人们也纷纷上书院捐献财产。在顺德的太平年景,经济窘迫的贫家子弟只要立志发奋读书,不受太多经济因素的制约。顺德科举甲于岭南,乡绅体系,功莫大焉。
顺德历史的文化社团也多由乡绅出资倡建,比较有名的是青云文社。青云文社由大良乡绅罗淳衍、龙元僖筹款置产,“殷实绅士”总理事务,“并孝廉八位协理,城乡各四位,递年轮请,以均劳逸”。文社既是绅士们休闲时酬唱呤咏的“俱乐部”,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下有田产数十顷,如有举子赴京殿试,所有费用均由文社支出;文社也向顺德在京官员发送“京官炭金”,送在冬季严寒的北京官员赠送暖气费,类似于今天的“跑部钱进”;如果秀才中举,每位可获奖学金白银50两;如果顺德人考取状元可获400两白银的奖学金、探花也可获得300两白银的奖学金……
乡绅们主导的教育的成功,使顺德历史上科举文化广东最盛,也使顺德的发展更少受地方官员和上级政府的制约,官员们行政的时候多数会考虑靠顺德教育网络支撑起来的官场人脉,这些乡绅网络客观上荫护顺德的发展。
至于交通、治安、敬老、恤孤、助残等公益事业,乡绅们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事例不胜枚举。
乡绅拐点
乡绅的产生,有赖于明清两朝“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在“皇权不下县”的制度框架下,“国家”通过察举、荐举、科举、捐纳等渠道,把地方精英吸纳到政权体系中,给予乡绅少量的税务优免、司法豁免权利,让他们尽到士民表率的责任,并藉此以低成本控制基层社会。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
乡绅体系源于传统儒家理念的社会共识,在一个共识溃败或缺乏共识的社会,无法产生贵族群体或乡绅群体。“五四运动”后,儒家共识全面崩盘,由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正能量衍生的“上对国家权力负责下对地方利益代言”的思维体系崩溃,乡绅体系在中国大陆全面进入衰退期。
除了社会共识之外,造就“乡绅精神”的土壤,必须是“小政府、大社会”。在一个“大政府、弱市场、无社会”的格局之下,再多的“代表”、“委员”,面临缺乏的公共社会空间,根本不能发挥自身章程规定的社会作用,更遑论孕育乡绅精神。
借鉴乡绅体系的香港太平绅士制度,在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仍然展示了勃勃生机。在拜物教沦为沦为社会共识的时代,在贵族精神被异化为特权、奢侈享受的时代,在一个社会空间暧昧未明的时代,在一个公共责任淡漠的时代,顺德和中国,都在期待乡绅精神出现拐点而后星火燎原。(作者:吴铭 自由撰稿人)
【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