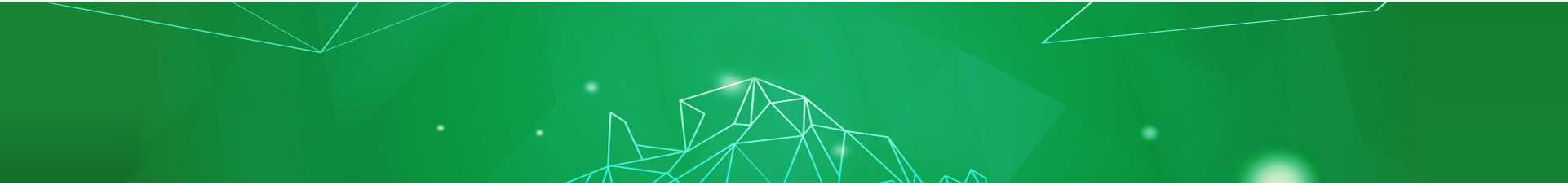
一、渊源回溯
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艰难困厄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每天划舟挥桨,渡河过江。他们每每要共同应对不时袭来的山岚瘴气,更要一起合力搏杀江边巨鳄,河中蛟龙。
许多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猛虎凶兽,或漩涡山崩,在毫无征兆的血腥生死或病痛分离中,他们只能守望相助,忘身救友,他们更只能在呼朋唤类,共同进退中渐渐形成奋不顾身,舍生取义,千金散尽,在所不辞的洒脱襟怀与不凡气魄,也渐渐学会联手共进,搏虎南山,并肩探源,逐兽山林,并在江边搭舍,燃火围坐中才得以逐渐安家立室,鸣犬相闻。
千百年来不断南迁的中原移民不仅带来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更带来中原正统醇厚的儒家观念,那周急济贫,积善成德,投瓜报李的胸襟与情怀,经千年风雨,已深深渗透在这片犹是一片滩涂的土地上。
一千多年来南越文化中粗犷但不失真率,耿直又充满人情味的文化特质与中原文化中深沉敦厚,关怀终极的文化特质相结合,再加上岭南文化独有的充满海洋气息的商业文化特质在传统文化与南越古风的长久熏陶下,更突现出其诚守信诺,急公近义的契约精神,而经过岁月的磨合与文化的融交,也水到渠成地构成义利兼和,济民善己,口碑广传,利商便贾的慈善文化。
三种文化与精神的结合,渐渐成为顺德慈善文化中最亮丽注目的特质,尤其是其回报社会的文化心理和实际行为,不仅令贫困民众获得及时实惠的支助与扶持,更在全社会形成乐善好施、奉献无求的良好氛围。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日渐繁荣,民众生活渐入佳境,人们手头资源日益积累,各种慈怀善行如春风吹绿野,无处不在。顺德商人们更通过各种慈善活动,以大笔资金回报社会。他们的精神更如阵阵春风,吹拂得绿茵处处,脆生生满布顺德大地,并让人们看到生命的春天、充满活力与激情的人生和充盈着爱心与慈善情怀的当代顺德,从中可让人梳理出漫长却清晰的精神脉络。
二、古代例子
顺德虽是鱼米之乡,但不时袭来的天灾却往往令粮食无收。民众家园顿失,无以为凭,致令嗷嗷待哺者满目皆是。
据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台风屡作,禾不登谷,因而米价腾贵,令“斗米百钱”,抢米风潮,屡禁不止。县政府马上开仓赈济,但杯水车薪,只能暂解饥困,难以为继,后来县内许多心善怀良的富户纷纷开仓,力助颠危,并且严监度量,按男女老幼分别给予赈济。
在天灾骤至,困厄饿饥时,人们犹不忘礼仪秩序,再加上捐助及时,令米价渐见平稳。这些捐资献米的巨商乡绅,并没留下自己名字,只如一阵清风,吹走人们心中阴霾,这使当时的县令刘鹏深为感动,他饱蘸浓墨,亲笔写下《阖邑赈饥论》记录其事,表彰其德。至今,这篇文章仍存县志,成为顺德人见难挺身,为善不彰的美德。
这位县官更赞扬顺德为“义乡”。因他看见人们平时“钟楼以定晨昏,建祠宇以表遗爱,修青云之路,文昌宫以储养人才,好善乐施之风冠于岭表”,而在风云突变,稻米歉收时,又能捋袖奋起,开仓济民,令这位见多识广的县令亦大为感叹,一定要写下此篇碑文,令这些无名义士随文不朽。
其实,在顺德,倾尽家财纾民困难的义举多不胜数。
雍正三年(1725年),西江水大,作物歉收。雍正四年(1726),米价日涨,当时的县令陈鸿熙初来顺德,见民难聊生,他怕毫无人际关系的自己无法号令县内富户,只好悄悄捐俸典衣,买米济民,后来县人得知,一片哗然。他们纷纷讲:难道你才能行善施惠?我们也很想捐资助困,只是没有您的指令而已,现在就让我们唯您马首是瞻吧。他们这些质朴的话语,令这位县官感慨万千,频频点头。很快,一大批热心富户分粮散户,井然有序,且船运求粮,散分乡村,顿解一时之困,顺德人的善举,令这位邑令既惭又喜,对这片土地有一个更直接而深刻的认识。
为富惠民,一直是顺德人,尤其是商人最为朴素的理念,因而,无论是古代赈灾还是近代济民,他们都出自近乎天性的自觉,不求回报,不求扬名,只求患唯相恤,有无相通,且形成父子相助,夫妻互勉的风气。虽然,古人常说这种善行可召祥禳灾,但顺德商人喜欢那句古语:积善之家,家有余庆。
深厚的传统文化,令古代富商再也无法将行善与行商清晰剥离,相反,他们发现,彼此交融,内心更纯净,目标更高远,事业,也更火红。
三、近代慈善
在清末,人们在旧寨乡太平山山腰上设立风雨茶亭,专供往来行人歇脚喝茶,常年供应凉茶的善举说不上是如何卓异不凡,但也折射出供茶送水者一片淡如清风的善心,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清代光绪年间,顺德各类早期的慈善机构日渐成型,越来越发挥其公益机构的应有作用。
光绪六年(1880)创办的大良义仓,本是由大良附近富户每亩捐钱一分主要组成。另外,义仓又向各处庙堂收取庙捐,先买谷储仓,再置业收租,以随时添购米谷,以备饥荒,其中的收款票据清晰明了,永作凭据,因而保证了义庄存米丰歉无忧,成为近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慈善机构。
其他乡镇亦仿效此法,如大洲乡的更日会,龙江乡的广惠社,龙江乡的仓田会等,都储米备荒,以达到济孤助寡,拨款赈饥的作用。
经过百年发展,顺德的慈善团体也渐成规模。如光绪元年(1877年)的桂洲灾义善社,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举济院,光绪二十七年(1907年)容奇的本仁善堂以及其后的养生善社,怀远义庄等,这些机构或收容贫孤,或赠医施药,或施药给粥,甚至是施棺送葬,成为孤独无助的弱势群体苟存性命,求医获药的唯一机构。
民国期间,顺德已拥有各类慈善机构几近二十,其中顺德赠医社、大良救伤队、容桂救群善社、大良同仁善社、大良济群善社、容桂的弃婴收育社、县社会服务处,勒流的溥仁善社等,这些发自内心,出自双手的民间慈善力量,有效地舒缓着因天灾瘟疫而令毫无回天心力民众的困境,并得以为他们提供一方略能安身存命之所。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县衙门设立“内务课”,专责民政事务,但由于顺德慈善工作一直都由民间人士主持,因而政府亦沿古法,仍由民间热心人士兴办。
民国初年,官方也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西中公医院免费施诊”、“大良平民医院”、“贫民教养所”,尽一切可能减轻因种种灾难而导致身心损害的民众。官方设立的内务科也渐渐以带有行政色彩的角色去主理募捐赈济、禁毒禁烟等活动,此时的慈善行为大多是以设立赈济机构,各种团体积极捐资捐物,另外便是以工代赈拨粮,并从义仓中提取款项购买谷米,但其主要力量仍来自民间富户,政府只充当运筹号召作用,因而在日伪时期,官吏从中克扣,执行不力,再加上天灾战争,其慈善意义作用渐失,而民间设立的孤老院、来苏院、育婴社、婴儿保育社等机构仍为老人及婴儿提供着力所能及的资助和帮扶,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如柏、青云儿童教养院,为当时流离失学的儿童开设学校,培育出一批自强出息的人才,在顺德慈善历史上写下他们值得称颂的篇章。
如今,我们难以追溯昔日顺德商人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为近代顺商慈善文化中留下一行行清晰而明快的注脚。
四、港澳顺商
经过近千年的文化积淀,当代顺德商人在时代新起点继续前行。
首先应该大书一笔的是港澳乡亲。解放初,他们无偿捐修家乡一批汽车以供生产与运输。六十年代,港澳乡亲捐资兴办顺德华侨玻璃厂,在经济困难的六十年代初,仍是这些顺德乡亲冲破重重困难为家乡代购化肥,且将所有贷物转化为投资,他们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在家乡一穷二白时不求回报地资助家乡。这种无私奉献,情系家园的精神与善举,使他们成为顺德建国后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慈善人物,并将在顺德慈善历史上永远铭刻上他们寻常的名字和不凡的贡献。
从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日渐完善,人们积富有余后,熏陶近千年的古老慈善文化迎来持续且蓬勃的发展。海外乡亲,港澳同胞就在顺德合资扩建中学、小学、图书馆、幼儿园,并设立教育基金,梁銶琚、李兆基、郑裕彤、胡锦超、刘胜昭、黎时暖、梁开等人捐资频频,在不断挺进但需要大量支持的顺德发展进程中注入了充满乡情的资金,更注入澎湃的精神力量,更引得众多大中小企业及个人踊跃捐资,无私奉献,逐渐将顺德慈善进程推向近千年来第一个全社会参与的高潮。
每次他们回乡讲话,那悠然古雅的未改乡音,那质朴无华的答谢致辞,寄托着一片深情与殷殷厚望,折射出承传千年,至今发扬光大的顺德水乡所特有的光风霁月与倾囊襄助,润物无声的洒脱襟怀:横跨两岸的桥梁、直通村尾的公路、余暇休憩的康乐中心、救济施药的乡镇医院、安度晚年的敬老院甚至是村头小孩嬉戏的塑胶地板,老人对弈饮茶的石凳石桌。他们无微不至,一诺千金,让全社会都享受到他们早年拼搏,如今回报社会的一片真情。
1985年,顺德政府部门采取集体出资,群众捐资,海外港澳同胞捐助的方式建成大良凤城敬老院及北滘碧江敬老院,这两所敬老院,花木扶疏,曲径碧池、房洁床净,服务周善,成为港澳乡亲捐福利设施的典范,至今仍口颂流播。
一直以来,乐从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乐从商会会长劳松盛曾表示:乐从人都热心慈善,每逢有慈善活动举行时,企业家都争相参与,踊跃捐款,本次慈善晚宴也不例外。乐从商会的企业家在得知晚宴举行的消息后,马上就认捐了39围。我觉得,慈善事业应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乐从慈善会成立秘书处,就是将慈善事业日常化的一件大好事。这意味着,将有专人、专门机构管理我们的慈善活动,乐从的慈善事业,将发展的越来越好。
千万巨额的善款不仅实现了古代贤圣“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高远理想,更达致慈善资本有效利用的目标,并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的完善与推行中为社会的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与持久的物质后盾,有力地推动各部门促进社会各项事业顺利发展,同时更在全社会形成慈善积德,帮扶弱小的良好风气,成为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文化解读
富有余财,力赠无助,善行育德,乐善无求已形成当代顺德人的城市文化,更形种发自内心,听从本性的自觉行为,自然也是几十年政府引导融合,又经过三十年经济发展与腾飞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自觉与行为。
在近千年的顺德文化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及“一曰慈,二曰俭”的传统思想早已融入顺德文化,顺德商人在助人为善中寻求到奉献社会与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结合点,在伸手助弱,解囊扶贫中达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最佳结合。
经济的复兴,社会资本及民间财富初步积累后的今天,尤其几十年来文化断层所突显的传统文化缺席与价值观念的游移,令大众身处熊掌与鱼舍取不定,进退维谷的尴尬之中。此时,一部分清醒而慷慨的顺德商人用自己的财富与自觉行为对当代价值观念进行积极修补,并与传统文化道德真髓作真诚接续,在历史价值坐标与当下文化心态之间奋力构建着一个大众认同,又与传统道德内核融通的当代道德规范与观念体系,正如梁銶琚博士等一批杰出人物那样,他们一生积财巨繁,但慷慨捐助家乡建设,并致力于国内教育机构与文化基金的支持,不仅从物质和资金上进行实际支持,更从精神与文化的高度进行有力推动,从而更迅速地达到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与供给的吻合,形成公益文化的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梁銶琚、汤伟立、何杰文、美的、科龙、万家乐、格兰仕、莱尔斯丹、勒流港、爱心超市及大批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一批顺德商人内心深处,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与善德已越来越成为他们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观念中,财富越来越更多地体现为抽象的法律意义。
他们认为,那些超出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财富,其实已应属于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已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因而,正如卡内基所分析的那样,在他们看来,“处置多余的财富,让其真正服务并且益于社会,其实需要另一种智慧,一种比获取财富更高的智慧”,在他们的概念中,“致富的终极目标其实是将多余的财富回报给社会”,于是,尽可能让财富发挥具体而实际的效用,达到物质与金钱之外所能带来的精神满足,令这些财富让自己能体验到超越纯粹金钱效用的另一种生活与感受,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充满智慧挑战与胸襟考验的人生境界,因为它更需要捐赠者对未来的准确把握与自我价值的理性判断,但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与率先垂范的意义却毫无异议地成为这个时代的典范。
在河汊纵横、出门登舟的顺德,伴水相生、聪明灵巧的顺德人,自古至今深悟水性。因而,无论是穿石化岩,随势赋形的特质,还是趋低顺流,俯仰自如的品格,甚至是涌泉相报的本性,他们都深得神奥。那化灾为祥,集腋成裘,汇涓成河,汇涓成河的慈善胸襟与情怀更成为共同精神并上升为公益活动,他们与众多草根阶层一起,积极将财富转化为民众的实获惠福,并在大量细微而长久的慈善活动甚至是行为中自我感悟慈善的文化意义,令精神与灵魂得到提升与净化,构成一个庞大而纯粹的公益慈善队伍,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也可见出顺德作为经济发展的地区,慈善文化已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最鲜活与感人的当代文化与精神,而顺德商人,正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作者:李健明 文化学者)
【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